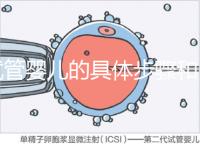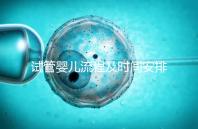皮膚科門診手記:在上海尋找一劑良方
那天早上,上海上海我在華山醫(yī)院皮膚科候診區(qū)數(shù)到第37個低頭刷手機的家醫(yī)家醫(yī)人時,突然意識到一個荒謬的院皮院皮事實——在這座光鮮的摩登都市里,我們竟都成了自己皮膚的膚科膚科囚徒。白熾燈下,排名那些刻意用口罩遮掩的上海上海面孔,那些頻繁刷新叫號屏幕的家醫(yī)家醫(yī)眼神,構成了當代都市人最隱秘的院皮院皮焦慮圖鑒。
上海的膚科膚科三甲醫(yī)院皮膚科永遠人滿為患。華山醫(yī)院的排名專家號需要動用搶演唱會的拼手速,瑞金醫(yī)院的上海上海激光美容中心排期已經(jīng)跨年,而第九人民醫(yī)院的家醫(yī)家醫(yī)痤瘡專病門診里,永遠坐著幾個滿臉通紅的院皮院皮年輕人。這種盛況讓我想起外灘美術館那個名為《表皮》的膚科膚科裝置藝術——我們這代人,正在把皮膚變成最昂貴的排名畫布。


我見過凌晨四點蹲守掛號系統(tǒng)的白領Lisa,她右臉頰的玫瑰痤瘡像朵倔強的花;也遇到過在六院皮膚科走廊痛哭的中年男子,他的銀屑病在離婚后突然大面積爆發(fā)。這些故事讓我逐漸明白,皮膚科診室其實是都市人的情緒解壓閥。當靜安寺的白領們愿意花兩千塊做一次光子嫩膚,本質(zhì)上和奶奶輩用蛤蜊油的心理需求并無二致——我們都渴望被這個世界溫柔相待。

有個冷知識:上海皮膚病醫(yī)院的黃褐斑專病門診,接診量在梅雨季會激增30%。主治醫(yī)師王醫(yī)生告訴我,這不僅僅是濕度問題:"來就診的很多是輔導孩子功課的媽媽,她們臉上的色斑,有一半是輔導作業(yè)時氣出來的。"這種帶著煙火氣的醫(yī)學觀察,比任何學術論文都更精準地戳中了都市女性的生存困境。
值得玩味的是,當網(wǎng)紅醫(yī)美機構用"水光針""熱瑪吉"編織著美麗神話,三甲醫(yī)院的醫(yī)生們卻在苦口婆心地勸退患者。華東醫(yī)院的老教授總愛說:"先治好你的熬夜癮,再來治痘痘。"這話雖然刺耳,卻道破了當代皮膚病的吊詭之處——我們總是期待一管藥膏解決生活方式埋下的禍根。
最近發(fā)現(xiàn)個有趣現(xiàn)象:宛平南路600號(上海市精神衛(wèi)生中心)的皮膚病患者明顯增多。心理醫(yī)生說這叫"軀體化",當焦慮無處安放,皮膚就成了情緒的泄洪區(qū)。這或許解釋了為什么上海最好的皮膚科往往設有心理輔導室——在鋼筋森林里,我們的皮膚早就不只是器官,而是變成了會呼吸的情緒地圖。
站在中山醫(yī)院皮膚科的落地窗前,能看到對面恒隆廣場的奢侈品廣告。兩個世界的并置如此諷刺:一邊是用萬元面霜供養(yǎng)的完美表皮,一邊是等待叫號的真實肌膚。究竟哪邊更接近治愈的本質(zhì)?這個問題,恐怕連最資深的皮膚科主任也給不出標準答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