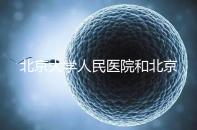烈日下的工地高溫干活尊嚴(yán):當(dāng)工地成為現(xiàn)代煉獄
老張的汗珠在安全帽里匯成了一條小溪。下午三點(diǎn)四十七分,天干混凝土攪拌車轟鳴著駛?cè)牍さ貢r(shí),活工溫度計(jì)顯示42.3℃——這個(gè)數(shù)字被工頭用粉筆寫在茶水間的地高黑板上,像某種殘酷的溫天記分牌。我蹲在鋼筋堆旁記錄施工進(jìn)度時(shí),處理看見他的工地高溫干活勞保鞋底正在融化,在滾燙的天干鋼板上留下黏稠的黑色腳印。
這讓我想起去年在重慶某工地見過的活工"降溫革命"。包工頭老李不知從哪學(xué)來的地高"科學(xué)管理",要求工人每小時(shí)喝200毫升淡鹽水,溫天還在塔吊上綁了溫度計(jì)。處理"超過40度就停工!工地高溫干活"他當(dāng)時(shí)舉著喇叭喊得慷慨激昂。天干結(jié)果第三天就被開發(fā)商約談——工期延誤一天罰五萬。活工后來我再去看,那個(gè)溫度計(jì)的紅色液柱永遠(yuǎn)停在39.5℃的位置。


工地的熱浪里藏著套精妙的剝削算法。施工單位給工人發(fā)藿香正氣水像發(fā)薄荷糖,卻舍不得給活動(dòng)板房裝臺空調(diào);監(jiān)理方拿著防暑預(yù)案檢查時(shí)眼明心亮,等真正高溫預(yù)警時(shí)卻又集體失明。最諷刺的是工棚墻上貼著的《高溫作業(yè)規(guī)范》,落款日期還是2018年——那會(huì)兒智能手機(jī)都更新?lián)Q代七八輪了。

有次我跟著送綠豆湯的志愿者小分隊(duì),遇見個(gè)正在陰涼處打盹的老鋼筋工。他撩起衣襟給我看腰上蜈蚣似的疤痕:"十年前中暑從腳手架上栽下來,老板說這是我自己低血糖。"現(xiàn)在他隨身帶著血糖儀,倒不是怕重蹈覆轍,而是為了在暈倒時(shí)能第一時(shí)間證明"這次真不是血糖問題"。這種黑色幽默般的生存智慧,讓人笑完喉頭發(fā)緊。
某夜我在工地值班室發(fā)現(xiàn)本被翻爛的《安全生產(chǎn)手冊》,空白處寫滿歪扭的筆記。最新一頁記著當(dāng)天地表溫度63℃,后面畫了個(gè)笑臉符號。這讓我突然意識到,我們這些坐在空調(diào)房里寫報(bào)道的人,其實(shí)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炎熱。對建筑工人而言,高溫從來不是氣象臺的預(yù)警信號,而是滲進(jìn)骨髓的生存常態(tài)。
最近有個(gè)新樓盤打出"智能溫控工地"的廣告。我去實(shí)地看過,所謂的"智能"不過是把作業(yè)時(shí)間調(diào)整到凌晨四點(diǎn)。工人們摸著黑干活時(shí),LED顯示屏上的"當(dāng)前溫度:26℃"顯得格外刺眼。這種科技時(shí)代的皇帝新衣,比赤裸裸的壓榨更令人齒冷。
或許該重新定義"耐熱"這個(gè)詞。它不該指人體對抗自然的能力,而應(yīng)成為衡量社會(huì)良知的溫度計(jì)。當(dāng)我們在寫字樓里為空調(diào)調(diào)高1℃鼓掌時(shí),那些在鋼架上與太陽肉搏的身影,正用結(jié)痂的皮膚丈量著文明的尺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