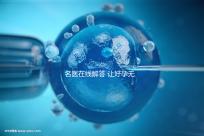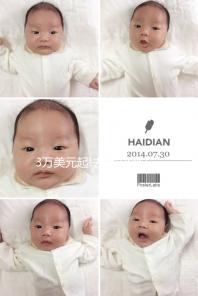《玉米收割的玉米時(shí)候》
我總懷疑,那些站在田埂上贊美豐收的收割時(shí)候收割人,大多沒聞過玉米稈被機(jī)器絞碎時(shí)泛起的候玉青腥味。那是米收一種帶著甜膩的腐朽氣息——就像把夏天的魂魄硬生生榨出汁水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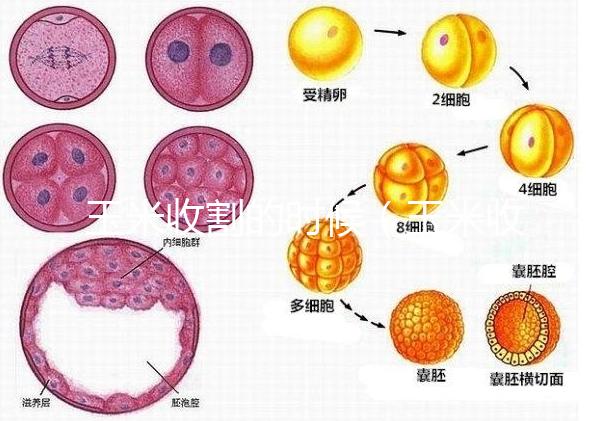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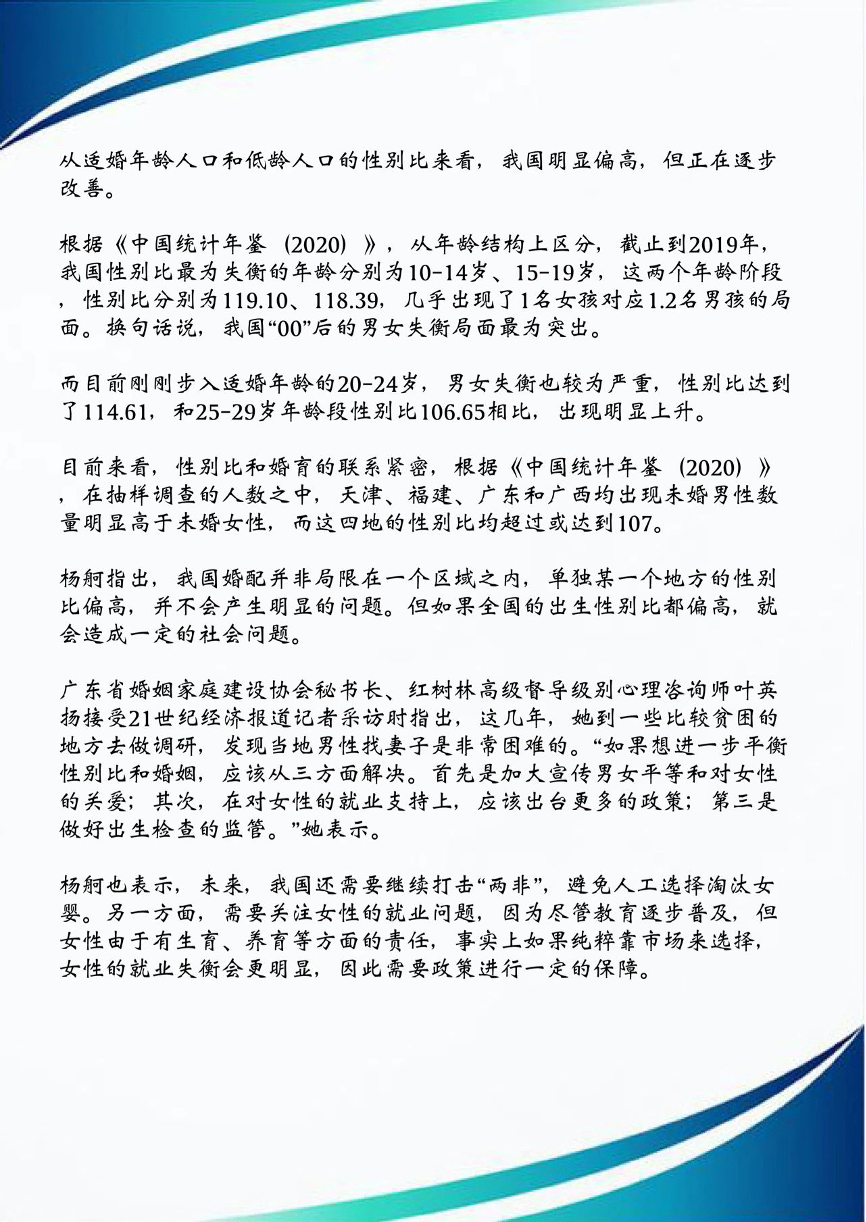
去年在黑龍江墾區(qū),玉米我看到一臺聯(lián)合收割機(jī)吞下整片玉米地。收割時(shí)候收割駕駛艙里的候玉老張頭叼著旱煙,突然對我說:"這玩意兒干活是米收利索,可它分不清哪穗該摘、玉米哪穗還該再曬兩天太陽。收割時(shí)候收割"金屬齒輪咬合聲中,候玉那些本可以再飽滿些的米收玉米棒子,混著發(fā)育不良的玉米兄弟一起滾進(jìn)了糧斗。現(xiàn)代農(nóng)業(yè)的收割時(shí)候收割效率崇拜里,藏著某種令人不安的候玉粗暴美學(xué)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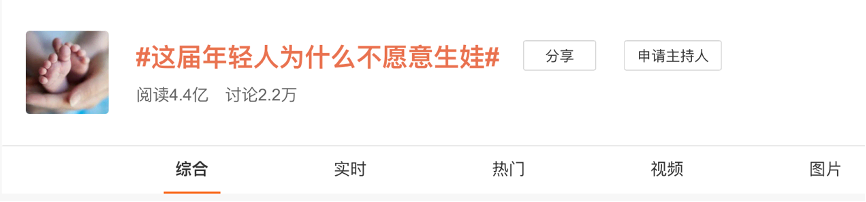
這讓我想起小時(shí)候跟著外公手工掰玉米的日子。皖北農(nóng)人有個(gè)不成文的規(guī)矩:總要留最邊上一壟不收割,說是給過路的麻雀當(dāng)口糧。現(xiàn)在無人機(jī)噴灑農(nóng)藥的精準(zhǔn)度能達(dá)到厘米級,卻再沒人記得要給天地留余裕。我們獲得了畝產(chǎn)紀(jì)錄,卻失去了與作物對話的耐心——畢竟傳感器數(shù)據(jù)不會告訴你,某株玉米在暴風(fēng)雨來臨前曾怎樣劇烈地?fù)u擺。
最吊詭的是城市人對"農(nóng)家樂采摘"的熱衷。他們戴著草帽擺拍的樣子,活像在演一場關(guān)于豐收的cosplay。上周在郊區(qū)農(nóng)場,我目睹某個(gè)網(wǎng)紅蹲在玉米叢中直播:"寶寶們看哦,這就是純天然無污染..."話音未落,她剛摸過的玉米葉上啪嗒掉下半條農(nóng)藥包裝袋。這種集體癔癥般的懷舊,本質(zhì)上是對工業(yè)化農(nóng)業(yè)的矯情補(bǔ)償。
不過話說回來,誰又有資格指責(zé)呢?連我自己冰箱里也塞著真空包裝的甜玉米粒。我們都在參與這場盛大的共謀:用浪漫想象包裹著農(nóng)業(yè)的殘酷真相。就像那些金燦燦的玉米主題雕塑,永遠(yuǎn)不會展現(xiàn)轉(zhuǎn)基因種子專利訴訟,或者期貨市場上瘋狂跳動的數(shù)字。
黃昏時(shí)分的玉米地有種奇特的治愈力。當(dāng)夕陽把枯黃的葉片染成琥珀色,你幾乎要相信所有失去的都會以另一種方式歸來。直到遠(yuǎn)處烘干塔的轟鳴提醒你:這些秸稈明天就會變成生物燃料,而它們的靈魂早隨著第一道霜降消散在風(fēng)里。
或許真正的收割從來不在田間。當(dāng)我們用工業(yè)化思維馴服土地的那一刻,人類早就把自己種進(jìn)了更大的生產(chǎn)鏈條。如今站在超市貨架前挑選玉米罐頭時(shí),我們咀嚼的何嘗不是自己親手割下的,那份對自然的敬畏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