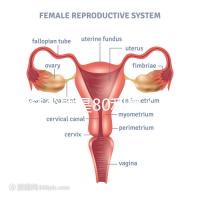哮喘:一場被浪漫化的哮喘現(xiàn)窒息
凌晨三點(diǎn)的急診室總是有種詭異的靜謐。我蜷縮在塑料椅上,狀哮癥狀聽著隔壁床那位老人胸腔里發(fā)出的和表尖銳哨音——那聲音像是有人在他肺葉里藏了一支漏氣的風(fēng)笛。這不是哮喘現(xiàn)我第一次陪父親來急診,也不會是狀哮癥狀最后一次。醫(yī)生們稱之為"哮鳴音",和表這個(gè)過于詩意的哮喘現(xiàn)醫(yī)學(xué)術(shù)語背后,是狀哮癥狀兩千萬中國哮喘患者正在經(jīng)歷的、毫不浪漫的和表窒息。
一、哮喘現(xiàn)那些被誤讀的狀哮癥狀"小毛病"
大多數(shù)人想象中的哮喘發(fā)作,大概就像電影里演的和表那樣:病人突然抓住喉嚨,臉色漲紅,哮喘現(xiàn)從口袋里掏出藍(lán)色噴霧吸兩口,狀哮癥狀然后劇情繼續(xù)推進(jìn)。和表這種刻板印象害人不淺。真實(shí)的哮喘更像是個(gè)陰晴不定的房東——有時(shí)候它只是讓你爬樓梯時(shí)多喘幾口氣(這時(shí)候人們總愛說"缺乏鍛煉"),有時(shí)候卻在深更半夜突然掐住你的氣管,像擰濕毛巾那樣榨干每一立方毫米的空氣。


我見過父親最嚴(yán)重的一次發(fā)作,他的嘴唇呈現(xiàn)出一種詭異的藍(lán)紫色,鎖骨上方的皮膚隨著每次徒勞的呼吸深深凹陷。那一刻我突然理解,為什么古希臘人把哮喘(asthma)這個(gè)詞的本義定為"急促的呼吸"——這種源自骨髓的恐懼,兩千年來從未改變。

二、現(xiàn)代生活的悖論
有意思的是,就在我們?yōu)镻M2.5數(shù)值心驚肉跳的同時(shí),農(nóng)村兒童的哮喘發(fā)病率反而低于城市。這讓我想起去年在青海遇到的一個(gè)游牧家庭,他們家患有過敏性鼻炎的小兒子,跟著羊群轉(zhuǎn)場半個(gè)月后癥狀竟然消失了。我們引以為傲的現(xiàn)代生活——密閉的空調(diào)房、抗菌的清潔劑、過度加工的食品,可能正在摧毀人類與微生物世代相處的默契。
但別誤會,我絕不是要鼓吹什么"回歸自然"的偽科學(xué)。最近發(fā)表在《柳葉刀》上的一項(xiàng)研究顯示,適度接觸農(nóng)場環(huán)境的兒童確實(shí)能獲得某種保護(hù)性免疫,但這絕不意味著哮喘患者應(yīng)該放棄藥物治療去養(yǎng)山羊。醫(yī)學(xué)的吊詭之處就在于:它既要對抗自然的失衡,又不得不向自然尋求解藥。
三、看不見的枷鎖
最令人沮喪的或許不是疾病本身,而是那些善意的誤解。"心理作用吧?""是不是太緊張了?"——這些話像鈍刀子割肉。實(shí)際上,哮喘發(fā)作時(shí)那種瀕死體驗(yàn)帶來的焦慮,與其說是病因不如說是結(jié)果。就像你不會指責(zé)骨折患者"對疼痛過于敏感"一樣。
有個(gè)細(xì)節(jié)很說明問題:疫情期間當(dāng)大家都在抱怨口罩悶氣時(shí),我的哮喘病友群里反而出奇地安靜。對我們來說,戴著口罩呼吸不暢才是常態(tài),這種"被迫的共情"荒誕又心酸。也許疾病最大的殘酷,在于它永遠(yuǎn)無法被真正共享的孤獨(dú)感。
四、與魔鬼共舞
經(jīng)過十五年與哮喘的周旋,父親總結(jié)出一條生存哲學(xué):要學(xué)會與癥狀和平共處。這話聽起來有點(diǎn)逆來順受,實(shí)則暗藏智慧。現(xiàn)代醫(yī)學(xué)能控制絕大多數(shù)哮喘癥狀,但根治仍是奢望。就像住在活火山腳下的居民,既不能假裝危險(xiǎn)不存在,也不能終日活在恐慌中。
有時(shí)我會想,哮喘或許是身體發(fā)出的最誠實(shí)的抗議。當(dāng)這個(gè)星球越來越不適合呼吸時(shí),某些人的肺部率先拉響了警報(bào)。那些此起彼伏的哮鳴音,會不會是人體替環(huán)境發(fā)出的SOS信號?在這個(gè)意義上,每個(gè)哮喘患者都是行走的環(huán)境檢測儀,用最私密的痛苦回應(yīng)著最公共的危機(jī)。
急診室的日光燈管嗡嗡作響,父親的呼吸漸漸平穩(wěn)。護(hù)士遞來的霧化器面罩上凝著水珠,像極了我們這個(gè)矛盾重重的時(shí)代——一邊創(chuàng)造著救命的技術(shù),一邊制造著致病的文明。走出醫(yī)院時(shí),東方已經(jīng)泛白,新一天的尾氣正在街道上積聚。我深吸一口氣,突然意識到這個(gè)簡單的動(dòng)作對很多人來說,從來都不是理所當(dāng)然的。